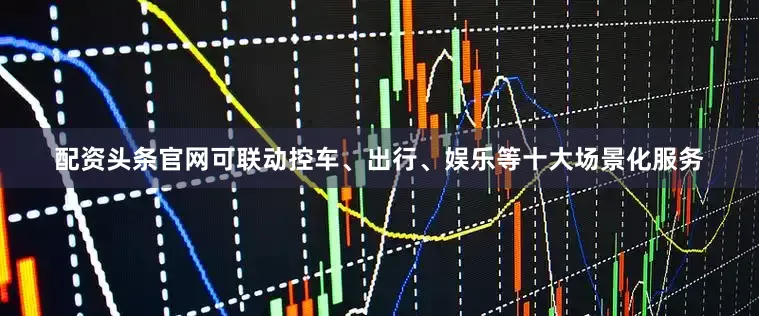配资专业网上炒股有些穷苦农民也离开了“大刀会”

打倒横行霸道的“五虎恶帮”
闽东苏区快速崛起后,连根据地周边的地主豪绅都纷纷组织起民团“大刀会”,对革命队伍发起了猛烈反攻。那时候,对苏区威胁最严重的正是这些反动民团“大刀会”。

所以,中心县委作出决定,让红军、游击队还有“红带会”一起发力,相互协作,按计划去消灭那些地主组建的反动民团“大刀会”,灭掉他们反革命的猖狂劲头。
福安东边和霞浦西北的山区交界处,藏着个西家宅村。这村里的“大刀会”其实叫“白鹤会”,领头的是三兄弟,再加上俩堂兄弟,被大家叫做“五虎”。这五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凶得很,一年到头都练武,在村里横行霸道。他们老去攻击我们的苏区,干尽坏事,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他们还管着周围几十个“大刀会”的小团伙,铁了心要跟共产党对着干。
听说,西家宅“白鹤会”的武器是带铁钩的梭镖,这东西扎进人身体能把肠子和肉都勾出来。为了应对,我们自制了一种土家伙来对抗。我们砍来好多竹子,长度比梭镖多出三分之一,竹子上的枝杈留下七八寸长,用火烤热后,再泡到尿里增加硬度。打仗时,一根竹枝配上一把梭镖或者一支长枪。等敌人冲过来,先用竹枝把敌人刺来的梭镖卡住,然后我方梭镖立刻刺向敌人,或者用枪把敌人打趴下。
但我们只钻研了战术,却对敌人的真正实力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在未充分摸清情况时,就仅派六七十人去进攻西家宅。我们下午启程,等到达西家宅并将“大刀会”驻地团团围住时,天色已近五点。发起攻击时,敌人紧闭大门,躲在祠堂里毫无动静。我随部分队伍守在祠堂后门,正瞧见一名队员爬上了屋顶,打算往屋里投掷土制手榴弹。
猛然间瞧见,另一拨“大刀会”的人正飞快朝祠堂冲来,我们赶紧往后逃。
此刻,祠堂的后门猛地被推开,里面的“白鹤会”成员高声呼喊着,径直朝我们猛冲过来。
敌人眼看就要追上我,那梭镖尖离我就剩不到两米远,我心想这下糟了,肯定得死在这儿。就在这危急关头,一个人从我背后猛地冲过来,拽着我就往前狂奔,我一看,嘿,是赖金彪!后面追的刀匪大声吼着:“别让他们跑了!”赖金彪赶紧扔出一颗土制手榴弹,刀匪们看到飞来的手榴弹,吓得赶紧趴在地上。
可这炸弹偏偏是个没响的哑炮,刀匪看没炸,又发疯似的追过来。这时候,我们已经抢到了时间,跑到山脚下了。我们安排在山腰的接应人员,开枪打向刀匪,撂倒了好几个,剩下的这才慢慢退了回去。
回到山上后,众人复盘这场战斗,都觉得这次栽跟头主要是因为太轻视对手了。虽说没人受伤或牺牲,可这结果实在不光彩,让“白鹤会”那帮人更加张狂了。这简直是在给对手打气,让自己人泄气。大家心里都憋着股气,铁了心要把那“五虎”给收拾掉!
第二次,我们调来了红十六连,再加上东区的“红带会”成员,总共有三百多人,气势汹汹地朝着西家宅进发。这次,我们调整了作战策略,先派一小部分“红带会”的人去挑衅,引诱“大刀会”的人出来,故意装作打不过。等把“大刀会”的人引到空旷的地方后,大部队再围上去消灭他们。这次,我站在半山腰上看他们打仗。
“白鹤会”压根儿不把“红带会”当回事儿,我军先头部队朝村子冲去时,他们就气势汹汹地迎了出来。一个个张狂得很,乱喊乱叫的,第二线的红军立马冲上前,先用竹竿迎敌,架住了对方的梭镖,紧接着梭镖队冲向持刀的匪徒,一下便刺倒了好几个。匪徒们往后退,红军战士趁机朝他们开枪,又撂倒了一批。
“五虎”那几个家伙气急败坏,抡着大刀又带着人冲了过来。赖金标赶紧下令,集中火力,先把冲在前面的“白鹤会”头目给干掉。结果,横行一时的“五虎”兄弟,全被红军战士当场打死。剩下的那些刀匪一看“五虎”都死了,立马作鸟兽散,全都逃命去了。
把名头响亮的西家宅“大刀会”打垮后,周边各个“大刀会”据点的人都对红军怕得不行。有些“大刀会”据点自己就散了,有些穷苦农民也离开了“大刀会”,就剩下少数死心眼的“大刀会”还跟红军对着干,可最后还是得落个被消灭的下场。
闽东苏区打掉了好多在根据地周边捣乱、甚至跑到苏区里面搞破坏的地主反动民团“大刀会”,这样一来,苏区的局势就稳当了,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也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闽东特委召开会议,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1934年4月上旬,宁德县委书记叶国珍在福州被抓后变节,福建临时省委的代理书记陈之枢等人也因被捕而叛变,导致临时省委和福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受重创。闽东以及连江、罗源的党组织都与上级失去了联络,连上海的党中央也联系不上。于是,福安中心县委和连罗县委在柏柱洋共同开了个联席会议。
两边都觉得,要是和上级断了联系,得赶紧成立个统一的领导班子,好让这片地方的管理、协作更顺畅。所以,就打算把福安的中心县委和连罗的县委合起来,弄个中共闽东的临时特委。大家商量了一下,还投了票,最后选苏达当书记,因为他出身工人,之前还是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被派到连罗做特派员呢。那时候,党内有个心照不宣的规矩,就是党委书记得是工人或者贫雇农才行。组织部长嘛,就让我来当,宣传部长就由叶飞兼任了。
大家都觉得,闽东那边五个县差不多连成一块儿,已经初步有了苏维埃地区的样子。接下来,得加强闽东和连罗那边的海上联络,让闽东各个县都紧密联系起来。要是敌人从海上打过来,我们就往山里跑;敌人要是攻打山区,我们就去海上打游击。
特委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柏柱洋斗面村一个大地主家的宅院里。不久后,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柱洋顺利举行,四百多名来自全区各地的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齐聚一堂。会上正式宣告“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是马立峰,副主席是叶秀蕃,秘书长为张少廉。闽东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当时已成立的福霞、福寿、安德、安福、连江,以及随后成立的罗源、周墩、霞鼎等九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四十多个区级苏维埃政权。
闽东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是闽东百姓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历经长久拼搏、激烈战斗才赢得的成果,这成果是江平、成全、范浚等众多,甚至还有许多无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点也选在了柏柱洋斗面村内另一座逃亡大地主留下的宅子里。斗面村虽不大,却因位于柏柱洋的心脏地带,成了闽东革命的指挥核心。闽东红军独立二团在村中设立了他们的后方指挥部。同时,共青团闽东特别委员会和闽东妇女工作团的办公室也都设在了斗面村。
到了福安后,我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整天忙个不停,东跑西颠地工作。休息时间少得可怜,觉也睡不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样紧绷又劳累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我终究还是撑不住病倒了。原来在闽南漳州工作时得的疟疾,又找上门来了。
疟疾一发作,人可真遭罪。刚开始冷得要命,大夏天裹着棉被,牙齿还直打架,浑身哆嗦个不停,紧接着就发起高烧,体温能飙到四十度上下,烧得人晕头转向,而且隔一天就发作一回。那时候,除了金鸡纳霜丸,没别的药能快速见效。可这药是从国外进口的,农村根本不好买。
在闽东特委成立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疟疾,一直高烧不退。有时候,脚底板会突然涌起一股热流,随后全身就开始打哆嗦,牙齿咬得紧紧的,连嘴唇都被咬破了。眼睛瞪得老大,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虽然心里还明白,但就是说不出话来。
大家看到这情形,都慌了神,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大夫。正急得不知怎么办时,房东却挺镇定,找来了麻油,把艾叶和姜块用麻油炸得热乎乎的。接着,用这热麻油在我身上用力搓揉,再给我盖上棉被,过了大概俩小时,抽搐才慢慢好了。
那时,特委正开着一个关键会议,我生病了,没能去参加。后来任铁锋跟我讲了会议内容。会上,大家指出任铁锋在军事指挥上没有整体规划,只凭自己勇敢,就独自带队行动;还不遵守组织规矩,不尊重叶飞、詹如柏、马立峰这些特委领导,只听曾志的。詹如柏还批评说:“我们跟任铁锋说啥他都不听,得让曾志去说才行,这种相处方式太不对劲了。”
马立峰讲道:“曾志和任铁锋、叶飞走得很近,这在干部和群众里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做法。你们都是特委的重要干部,都得好好反思。曾志得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光批评,还得给她点处分……”虽说马立峰说了这些,但我心里明白,真正在背后推动这事儿的是詹如柏。
开完批判会,关于会上讨论的那些事儿,特委里没一个领导主动来找我聊过,这事儿还是任铁锋后来跟我说的,从那以后,叶飞就再也没单独找过我谈话了。
这次会上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处罚,而是作出决定,让我去福霞县同时担任县委书记一职。
那时候,福霞那块地方成了敌人重点进攻和“围剿”的地带,局势非常紧张。我恰好又生了一场大病,这个安排其实就等于给我处分,甚至算得上是很重的处罚了。
那时,我实在搞不懂,为啥要我担主要责任?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的?我根本没去招惹他们,不过,我得承认在这事儿上我确实有点小资的浪漫想法,我觉得恋爱是我的自由。
任铁锋和我在很多事情上看法都差不多,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很信任我,也很尊重我,所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不过,我其实不太喜欢他这个人,因为他有时候太粗暴了。我对叶飞印象不错,但心里也有点顾虑,他性格很倔,特别是对女同志,总有点大男子主义。

那时候,我和他们俩走得挺近,下班后经常一起玩,这也挺平常的。
陶铸在信里提到,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当时我才二十三岁,身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者,为革命献身是我随时可能面对的事;而且我早已把“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这些封建思想扔得远远的了。所以,再找个伴侣是我的自由,我有权自己决定。
我心里琢磨着,随它去吧!挨批就挨批,往后这类事儿我再也不管了,专心把工作干好。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
广禾配资-炒股配资手机版-配资免费体验-国内前十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网上在线配资炒股公司2016 年 12 月
- 下一篇:没有了